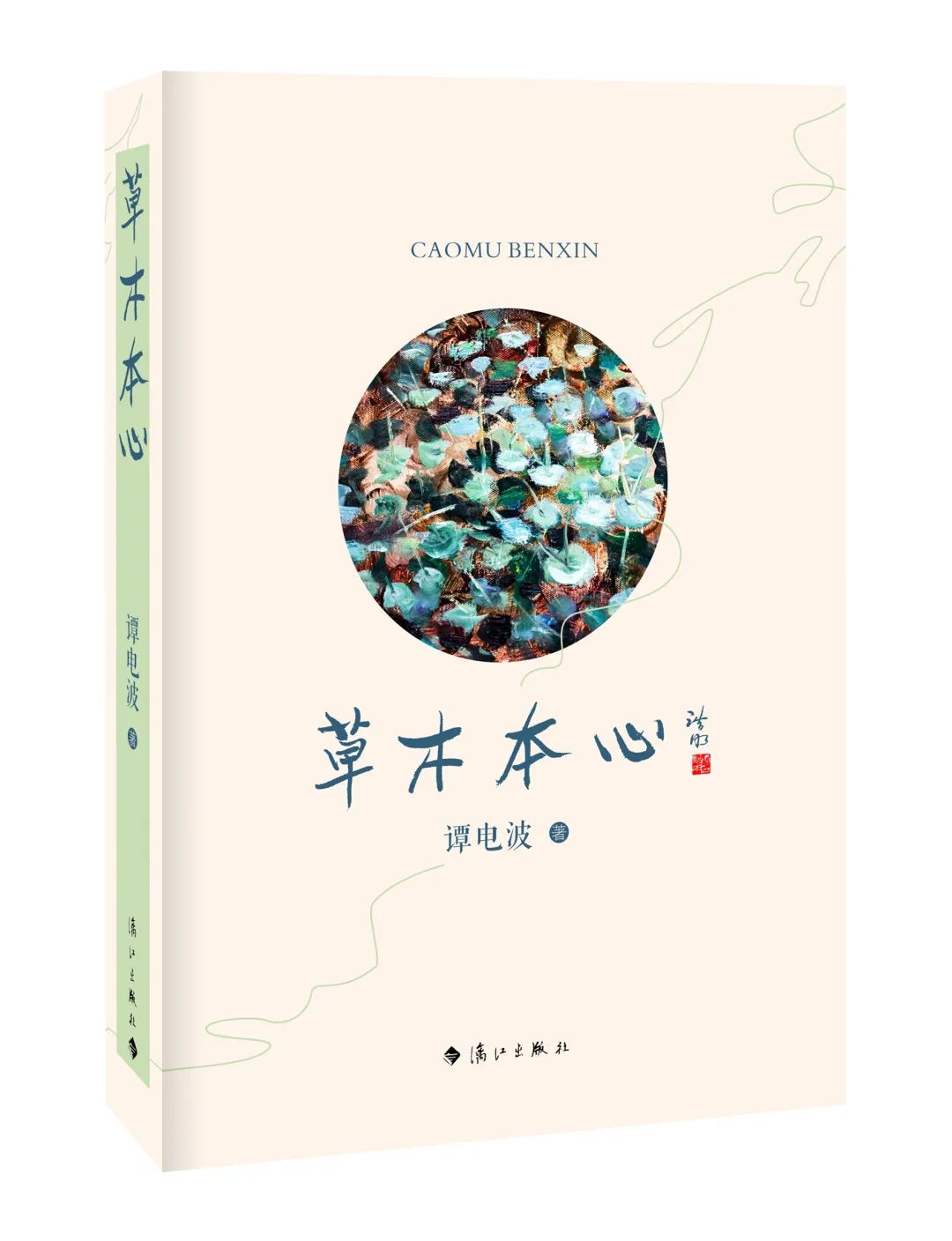
文|王丽君
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,中医药与古典诗歌始终是两条交织的重要脉络。它们一方面关乎身体与自然的辩证,一方面关乎情感与精神的表达,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。谭电波的诗集《草木本心》正是这一基因的当代显影——它以医者之思、诗人之笔,融汇三十余年的临床经验与文化沉思,将本草的药性与诗性的灵光完美结合,构建了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、物质与精神的文化桥梁。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中医药文化的诗意重构,更是对当代人精神荒芜的一种温和疗愈。
以诗为镜,让中医药文化的灵性再现
《草木本心》的创作根基深植于中医药学的沃土。谭电波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中医药工作的医者,对草木药材的熟悉与敬畏远超常人。然而,他并未止步于专业的药理分析,而是以诗意的语言重新诠释本草的生命力。全书分为“中药物语”“花语倾情”“本草一味”“满园药香”等八辑,收录220首诗歌,每一首都像一味精心炮制的药材,既有药性的严谨,又有诗性的自由。
在《紫苏,一切恰到好处》中,他写道:“紫苏的叶脉里流淌着夏天的风,疏解淤滞,如同解开时光的结。”这里,紫苏的药用价值“解表散寒、行气和胃”与诗意的意象“夏天的风、时光的结”浑然一体,让读者在审美体验中悄然接受文化的浸润。而在《黄连苦噢》中,他则以“苦”为媒介,追问生命的本质:“苦是药性,也是人生;黄连入口,唤醒的是舌根,还是心根?”这种由物性到哲思的升华,正是中医药文化与诗歌艺术共通的精髓——它们都致力于在现象世界中捕捉本质的力量。
谭电波的创作延续了中国古代“药名入诗”的传统,如辛弃疾《定风波》中的“木香”“防风”,但他并未停留在文字的表层,而是通过现代性的反思,赋予这一传统以新的深度。例如在《艾叶,款款而来的香草美人》中,他写道:“焚烧的烟雾里,淤塞的穴位开始星群闪烁。”艾草的热性与灸疗的仪式感,被转化为一种精神性的意象——星群的闪烁既是对经络畅通的诗意隐喻,也是对人类困境中希望之光的象征。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唤醒了文化记忆,更让中医药学从专业领域走向公共叙事,成为每个人均可感知的文化资源。
草木有情,让生态诗学与人文精神实现融合
《草木本心》的另一重价值在于其深刻的生态关怀。谭电波笔下的草木并非冷冰冰的药用材料,而是具有生命主体性的存在。他通过拟人化的书写,构建了一种“草木即人,人即草木”的共生哲学。在《卷柏,还魂草的简历》中,卷柏被描绘为“握住史前密码的生命哲人”,其耐旱与“还魂”的特性成为人类韧性的象征;而在《铁皮石斛的成长》中,石斛的顽强生长,“断崖上垂下黄金锁骨,每一寸都是与命运的谈判”,则被赋予孤勇者的气质。
这种物我交融的书写,既暗合了庄子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哲学观,也呼应了当代生态批评中“超越人类中心主义”的呼吁。谭电波的诗歌试图修复现代性带来的自然与文化的割裂。在《银杏叶的理想》中,他写道:“用空心的身躯盛满整个山谷的寂静”——银杏的空心既是其生物特性,也是一种东方智慧的隐喻,即唯有虚怀若谷,方能容纳万物。这种诗意表达,不仅是对植物生存策略的赞美,更是对人类文明过度喧嚣的批判。
此外,诗集中对草木“漂泊”“凋零”的描写,如蒲公英的“大善”、败酱草的“慈悲”,隐含了一种佛系的慈悲观。草木的枯荣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,而是与人类命运共鸣的生态寓言。在这种视角下,中医药学中的“天人相应”理论得到了文学性的诠释,而诗歌则成为生态伦理的启蒙媒介。
跨界共生,让传统文化走向新生路径
《草木本心》不仅是一部诗歌集,更是一场跨界艺术实践的成果。诗集中配有多位湖南画家创作的油画作品,实现了“诗画一体”的融合叙事。这种尝试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合作的“杏林香草”油画展一脉相承,旨在通过视觉艺术强化中药文化的感染力。例如《桔梗花,以爱谋生》一诗配以蓝紫色调的油画,桔梗的药用价值“宣肺化痰”与其花语“永恒的爱”在色彩与文字的互动中被同步传递。
这种跨界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,而是对传统文化传播困境的一种突破。中医药学长期以来被视为艰深晦涩的专业领域,而谭电波通过诗歌的柔化与艺术的渲染,让本草“活”了起来。在《冬虫夏草励志的故事》中,他将虫草的形成过程化为一种生命寓言:“动物与植物在死亡中达成契约,重生为药。”这种叙事既符合虫草的科学特性“真菌寄生”,又赋予其神话色彩,让读者在审美中轻松理解药性。
更重要的是,谭电波的创作揭示了中医药文化在当代传承的核心命题:创新性转化。从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到新冠肺炎中的“三方三药”,中医药始终在与时代对话。而《草木本心》的诗歌实验,正是用文学语言激活了传统药典中的“人性温度”。它让我们看到,中医药不仅是治病的术,更是养心的道——这种“道”需要艺术与人文的滋养方能持续生长。
本草即心,让生命意义实现诗性叩问
在诗集的终章《活在中药草本的血脉里》中,谭电波写道:“文字究其根本是幻觉,但我仍企图在语言中体验真相。”这句话揭示了《草木本心》的终极追求:通过诗性与药性的交融,逼近生命的本质。他对本草的凝视既是一种科学观察,也是一种哲学冥想。在《野山参的修行》中,野山参的生长被喻为一种苦修:“深埋地底二十年,只为一次破土见光。”这既符合野山参的采挖特性,也是对人类的礼赞。
而在《半夏正好》中,他捕捉了药材“半夏”的时空特性,即“夏至未至,半夏半生;药性在阴阳交界处平衡。”半夏的药用价值“燥湿化痰”与其名称中的时间性“夏季之半”,被巧妙转化为一种人生哲理——生命总是在半途之中,唯有平衡方能前行。这种由药性到心性的升华,使得《草木本心》超越了单纯的咏物诗,成为一部关于存在与意义的哲学诗集。
谭电波在后记中总结道:“单纯即是美,如同微笑。”这句话看似简单,却凝聚了中医药与诗歌的共同智慧,无论是治病还是治心,本质都是回归简单与自然。中医药强调“阴阳平衡”,诗歌追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,而《草木本心》正是将这二者融合为一种生活美学——它告诉我们,文化的传承不仅是知识的传递,更是一种生命态度的养成。
《草木本心》是一部多重对话的集合,有着文化传承的柔光。它与《黄帝内经》对话,挖掘医理中的诗性;它与《诗经》对话,延续比兴传统的当代活力;它与生态哲学对话,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;它更与每一个普通人对话,让中药文化从药房走向书房,从诊所走向心灵。
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中,传统文化如何避免成为博物馆中的标本?谭电波的回答是:赋予它艺术的形态与人文的精神。《草木本心》像一味药方,以诗意煎制,疗愈的不仅是身体,更是被异化的人心。当杏林香草的芬芳从古籍中飘入现代诗卷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诗集,更是一条文化复兴的路径——柔软,却充满力量。
来源:湖南文联
作者:王丽君
编辑:李香枝
 时刻新闻
时刻新闻